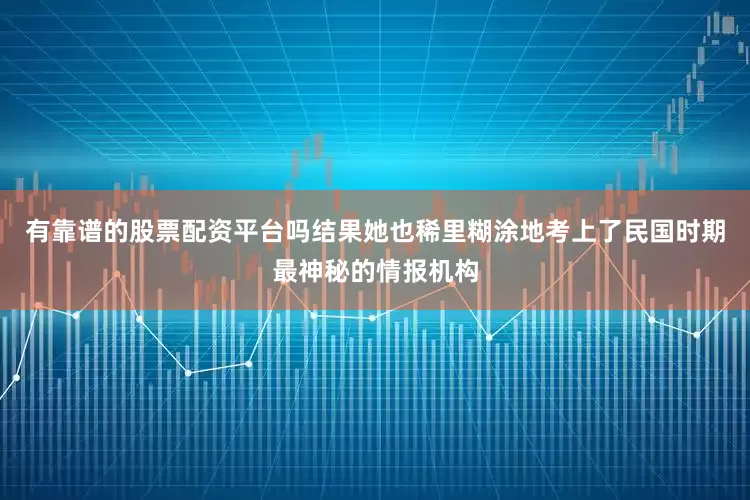
有个十五岁的农村姑娘,家里一直过得紧巴巴的,结果她也稀里糊涂地考上了民国时期最神秘的情报机构。几年过去,她变成了大陆唯一 remaining 的军统女译电员。
令人惊讶的是,她面对镜头时竟然说出了那句话:共产党养了我31年。

误打误撞进了译电科的那个江山姑娘
1943年春天,在浙江江山县,刚满15岁的王庆莲正为下一顿饭发愁。
父亲在她一岁那年就去世了,母亲独自一人抚养她长大,干着各种辛苦的活,苦苦撑了六年小学,终究挺不住了。

这个时候,军统局开始到江山招人了。
母亲毫不犹豫,就帮女儿报名了。
王庆莲问:“那军统到底是个啥?”
母亲说:那地方能吃上饱饭。
就这么点事,一个15岁的姑娘,连军统是做啥的都不清楚,就这样被卷进了历史的洪流。
江山其实是戴笠的家乡,军统里面有个默契:老乡优先。江山的话大伙平时听不懂,成了天然的保密屏障。王庆莲挺走运,和另外19个人一块被录取了。
6月8号,一辆军统的卡车把他们送到重庆,里面有4个女孩子和16个男孩子,平均年龄都还不到18岁。
王庆莲被派到磁器口造纸厂的密本股,听着挺高端,其实就是搞密码本的岗位,主要负责排写横码、竖码和角码,活儿烦死了。日本飞机天天轰炸,那密本股选在乡下,也算是为了保卫这些密码本,别出啥差池。

王庆莲在这儿干了整整八个月,每天的活儿基本上都是跟数字打交道。她根本搞不懂那些数字到底代表啥,也懒得去管,只要能吃饭,有工资领,那就挺好。
1944年4月,一线转变发生,王庆莲被调回军统局总部译电科华南股,那会儿算是迎来了个转折点。
这可不得了了,军统局本部在重庆罗家湾,戴笠的老巢,译电科就像是军统的核心,所有的重要电报都得在这儿处理。
王庆莲的军衔是准尉,不过工资却和少尉差不多,在那会儿,这份收入已经挺不错了。
她的直接上头是姜毅英,军统里唯一的女少将。这女人可不一般,曾破译过日本军方关于偷袭珍珠港的密电, 在那男人当道的军统里面,她算是个不折不扣的异类。
王庆莲的活儿挺简单,就是负责翻译电报。因为她会说江山话,许多用方言加密的电报,只有她能搞定。
第一次坐在译电科的办公室里,王庆莲有点发愣,屋里到处都是嘀哩哩的电报声,大家都埋头忙碌,气氛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
这就是译电科啊?她低声问身旁的同事。
办公室里突然笑成一片,一个15岁的乡村女孩居然不知道译电是什么。
姜毅英淡淡地瞥了她一眼:好好学习,别让江山的人丢了面子。

重庆岁月的两面人生
王庆莲后来提到,军统那三年,成了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。
白天在译电科上班,晚上则穿旗袍跳舞,简单说就是她在重庆的日子。

军统的任务压力挺大的,那阵子战事最激烈的时候,一周只能休半天假。王庆莲每天得应付几十份电报,内容丰富得很,有前线的战况、日军的动向、各地的情报信息。
她亲眼看到一份电报,上面写着日军在某个地方屠杀平民的消息,王庆莲看完之后气得直掉眼泪:这些日本鬼子,简直不是人!
姜毅英在一旁淡淡地开口:哭什么呢?把电报翻译清楚,比什么都更紧要。
王庆莲慢慢领悟到自己工作的真正意义,这些电报可不是普通的文字游戏,而是前线战士的生死讯息,是关系到抗战成败的关键情报。
每分钟翻译200个字,拿起毛笔写出细腻的小楷,王庆莲很快在译电科站站稳了脚跟。
戴笠有时候会过来译电科看看,王庆莲记得他,一向穿得利索,身上的中山装扣得一丝不苟,整得规规矩矩。
老板来了!有人低声嘀咕着提醒。

一瞬间,译电科变得鸦雀无声,大家都低头拼命专注工作,连呼吸都变得格外谨慎。
戴笠确实照顾着江山的老乡们,王庆莲想请假回家看望母亲,或者提前领点工资,戴笠都一向准许。江山的人们互帮互助,戴笠说,在外头过日子不容易。
下班以后的王庆莲,简直像变了个人似的。
她偏爱穿紧身的旗袍,涂上亮眼的口红,常去重庆的舞厅跳舞。在那个年代,跳舞可是主要的社交手段,军统里头也不例外。
王庆莲身材出众,长得漂亮,很快就在舞厅里成了瞩目的焦点。她喜欢那种被众人包围的感觉,也爱看着旗袍在旋转中摇曳生姿的美丽。
姜毅英实在看不过去她这一套。
有次,王庆莲涂了份特别亮眼的口红来上班,姜毅英当众训斥她:小姑娘,要是不努力点,可得把你关起来!
王庆莲的脸一下子红了,她清楚姜毅英不是开玩笑的,在军统这种单位,要关几个人都挺简单的。

从那时起,王庆莲在工作时变得更谨慎了些,可心里对姜毅英的怨恨却越积越深。
王庆莲觉得姜毅英嫉妒她年轻漂亮。译电科里有16个男人,4个女人,年轻的女孩自然更有人缘。虽说姜毅英是少将,可毕竟快40了,算是个年纪不小的女人。
这种微妙的职场氛围,最终成了王庆莲后来辞开军统的导火线。

和军统说再见后的人生转变
到1945年8月,日本宣布投降了。
军统局的任务重心逐步调整,许多人得分批返回南京,王庆莲因为平时表现平平,最后一批才轮到她留下来。

到了1946年7月,王庆莲才回到南京军统局总部报到,而此时的军统和在重庆的时候,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
戴笠在三月份乘飞机遇难之后,整个军统就变得群龙无首,各种势力都开始摩拳擦掌争夺地盘,王庆莲也觉得一种不详的预感逐渐弥漫开来。
姜毅英准备结婚去度蜜月,还打算长时间出门,临走之前,她又一次警告王庆莲:别让我失望,要不就关你禁闭。
王庆莲一听,心里就打鼓。在军统这种地方,一旦被关进禁闭室,出来后是什么模样可不好说,心里可是吓得慌。
8月的某天,趁姜毅英不在,王庆莲找个借口外出去一趟,说是要回家看望生病的母亲,组长听了也没多想,就批了。
王庆莲离开南京,回到了江山的老家,这一走之后,便再也没有返回过军统。
十八岁的王庆莲,就这样画上了自己在军统的篇章。

回到江山之后,王庆莲恢复了普通人的日子,她遇到了汪含芳,一个准备去浙江大学读书的年轻人,两人通过书信保持联系,感情很快变得亲密起来。
1948年3月,王庆莲和汪含芳喜结良缘,婚礼挺朴实的,她从未谈起过自己曾经的军统经历。
1949年,解放军渡过长江,王庆莲心里明白,新的年代已经到来。
她下定了一个很关键的决心,主动把自己是军统的人这事告诉了政府。
一开始,地方政府可是不信啊,觉得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,怎么可能是军统的译电员呢?
经过仔细核查后,政府确认了王庆莲的身份,调查结果表明,王庆莲只是做译电工作,从未卷入任何伤害共产党员的行动。

她在解放战争一开始之前就已经脱离了军统,政府认为她没有构成威胁,仍然可以过正常日子。
1951年,王庆莲陆续在杭州白肉市场和粮食局干活,尽力适应新的社会规则,想着变成一个普通的建设者。

农村翻新过程中,心里有些感慨:看到村庄一点点变样,心头那份满足和自豪真是难以言喻。毕竟,改变不止是景象的焕新,更是我们对未来的希望和努力的见证。每一砖一瓦,都凝聚着大家的汗水,也让人觉得生活更有盼头。走过这些年,深刻体会到,只有踏踏实实干,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;心里那份坚持,才是推动前行的最大动力。农村的变迁,也让我明白,任何地方的繁荣,都离不开大家团结一心的努力。
1958年,杭州拉开了政治整顿的帷幕,王庆莲主动请缨,愿意到农村去接受改造。
王庆莲坦言:“我了解自己的身份比较特殊,愿意到农村去努力争取,让大家看到我的真本事。”
一去就是整整23年。

农村日子确实不容易,王庆莲和丈夫被安排到偏远的山村,干着最繁重的农活,赚着最少的工分,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。
从1966年起,那段特殊的岁月成了王庆莲人生中最阴暗的时刻。
她那军统的身份又被翻出来,成了批斗的重点,每天参加会议批判,难免会动手打骂。
有次,一个大娘帮王庆莲换衣服时,发现她身上没有一块健壮的肉,全都是伤痕,大娘忍不住流泪了。
大娘别哭了,王庆莲安慰着她说,我已经习惯了,要是让别人看到你掉眼泪,还得挨打呢。
王庆莲的丈夫和儿子就住在离她不到100米的地方,可他们却见不到面,一家人被硬生生分开,各自忍受着煎熬。
在感到最绝望的时候,王庆莲曾想过轻生,她跳到了河里,不过被路过的好心人给救了上来。
想不开干嘛呢?救她的人这样问。
王庆莲叹了口气,说:“活着真挺难的。”
从那之后,王庆莲开始抽烟,每天一包,用尼古丁麻痹自己,减轻压力,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晚年。

到1978年,政策正式推行起来。到1981年,王庆莲的事情终于得到澄清,生活也逐渐回归正轨。
让她没想到的是,农村改造的那23年竟算作工龄,王庆莲领到了退休金,每月39元。
2010年,年过八十的王庆莲接受了记者的采访。
面对镜头,她坦率地表达了:我真的很感激共产党,党的照顾让我度过了31个年头,没有党,晚年的生活也不会如此安稳,这是我真心的话!
说这话时,王庆莲的眼眶里泛着泪花。
曾经那位军统的女译电员,走过了人生的高潮与低谷,最终心怀感激。或许,这就是历史另一种精彩的可能吧。

一个十五岁的农村女孩,机缘巧合成为了军统的译电员。多年以后,她不仅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,还变成了宽容与和解的代表。
她每天还是抽那一包烟,不过脸上的忧愁早已不复存在,岁月啊,真是最厉害的疗伤利器,也是最公平的裁判员。
王庆莲如今在杭州安家,过着平凡的退休老年生活,偶尔会有研究者前来拜访,她总是乐意配合地讲起那些年的事情。
那些都成了过去,她说,现在的日子让我挺知足。
配资资讯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南京股票配资平台双打能力已经从过去的“加分项”变成了“必选项”
- 下一篇:没有了


